-
6月22日
-
明代思潮之明代茶具的正文:
茶具发展是艺术化、文人化的过程,大体依照由粗趋精,由大趋小,由简趋繁,再向返朴归真、从简行事的方向运行。唐代茶具以古朴典雅为特点,宋代茶具以富丽堂皇为上等,明代茶具又返朴归真,转为推崇陶质、瓷质,但又比唐代的更为精致灵巧。明代茶书,记载了由宋至明茶具的变迁。蔡君谟《茶录》云:茶色白,宜黑盏。建安所造者绀黑,纹如兔毫,其坯微厚,〓之久热难冷,最为要用。出他处者,或薄或色紫,皆不及也。其青白盏,斗试家自不用。此语就彼时言耳。今烹点之法,与君谟不同,取色莫如宣定,取久热难冷,莫如官、哥。(张谦德《茶经》)宣庙时有茶盏,料精式雅,质厚难冷,莹白如玉,可试茶色,最为要用。蔡君谟取建盏,其色绀黑,似不宜用。(屠隆《茶说》)茶壶,窑器为上,锡次之。茶杯汝、官、哥、定如未可多得,则适意者为佳耳。(冯可宾《〓茶笺》)由于明代斗茶已不时兴,蔡襄时期的黑釉茶盏已很少使用。明代散茶流行,故其在今日,纯白为佳(许次纾《茶疏》),盏以雪白者为上,蓝白者不损茶色,次之(张源《茶录》)。绿色的茶汤,雪白的瓷具,清新雅致,赏心悦目,故明代瓷器胎白纹密,釉色光润,后来发展到薄如纸,白如玉,声如磬,明如镜,成为十分精美的艺术品。 但是,明代茶具最为后人称道的,不是艺术成就很高的白瓷,而是至今依然身价未减的江苏宜兴紫砂陶制茶壶、茶盏。紫砂壶最迟在宋代就已出现,当时胎质较粗,重在实用,多作煮茶或煮水。到了明代,由于发酵、半发酵茶的出现,特别是自然古朴的崇尚回归,唯美情绪的大力觅求,从一壶一饮中寻找寄托,使紫砂壶得到殊荣。阳羡名壶,自明季始盛,上者与金玉同价。(《桃溪客话》)吴中较茶者,必言宜兴壶。(周宕《宜都壶记》)历史学家王玲先生曾指出:一把好的紫砂壶,往往可集哲学思想、茶人精神、自然韵律、书画艺术于一身。紫砂的自然色泽加上艺术家的创造,给人以平淡、闲雅、端庄、稳重、自然、质朴、内敛、简易、蕴藉、温和、敦厚、静穆、苍老等种种心灵感受,所以,紫砂壶长期为茶具中冠冕之作便不足为奇了。#|L 明代周高起的《阳羡茗壶系》,是记载宜兴紫砂壶的最早文献。周高起字伯高,江阴(今属江苏)人,邑诸生,博闻强识,工古文词。明末,因抗声呵斥清兵的肆加箠掠而被杀害。他著有《阳羡茗壶系》和《洞山〓茶系》,两书常被合印在一起。《阳羡茗壶系》分为序、创始、正始、大家、名家、雅流、神品、别派,最后是有关泥土等杂记,还有周法高的诗二首、林茂之以及愈彦的诗各一首,作为附录。阳羡是宜兴一带的古名。书的开头说:茶至明代,不复碾屑、和香药、制团饼,此已远过古人。近百年中,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,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。陶曷取诸?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,能发真茶之色香味。紫砂壶体小壁厚,有助于保持茶香,发真茶之色香味,故受到欢迎。至名手所作,一壶重不数两,价重每一二十金,能使土与黄金争价。当时,宜兴紫砂壶就被珍视宝爱。gcd/` 据《阳羡茗壶系》记载,宜兴壶创始于当地金沙寺里的一个和尚,但他的名字已经失传。僧闲静有致,习与陶缸瓮者处,抟其细土,加以澄练,捏筑为胎,规而圆之,刳使中空,踵傅口柄盖的,附陶穴烧成,人遂传用。而促使紫砂陶制茶具这项发明走向艺术化的,也是一个无名小辈,他是学使吴颐山的书僮,只留下主人起的名字供春。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,供春随往侍奉主人。劳役之暇,他偷偷仿效老和尚做茶壶的技艺,亦淘细土抟坯,茶匙穴中,指掠内外,指螺文隐起可按,胎必累按,故腹半尚现节腠。这种腹上留有指节纹理的茗壶,周高起亲眼目睹后,慨然赞叹:传世者粟色,闇闇然如古金铁,敦庞周正,允称神明垂则矣!供春制的茗壶,流传于世的不多,号称供春壶。后来,他的子孙即以制陶为业,取供的谐音,以龚为姓。与供春一样被尊称为正始,即陶壶开创人的,有所谓四名家:董翰、赵梁(亦名赵良)、袁锡(或作元锡、元畅)、时朋(一作时鹏),均为明万历年间制壶高手。董翰文巧,其他三家多古拙。和四大家同时列入正始的另一名家李茂林,制小圆式,妍在朴致中,他还另作瓦囊,闭入陶穴,使烧火温度均匀,壶身颜色一致,壶面整洁干净,这一发明沿用至今。被《阳羡茗壶系》称为大家的,是时朋的儿子时大彬。他的创作发展过程,该书有较详细的介绍:初自仿供春得手,喜作大壶。后游娄东,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。 施茶之论,乃作小壶。时大彬如果只是一味模仿供春壶,仅仅在做工精良上下功夫,那是不可能被誉为惟一大家陶壶大师的,他的高明之处,是在聆听陈继儒等品茗论茶后,悟性极强,豁然开窍,创制了小型陶壶。他的制作,或陶土,或杂〓砂土,诸款俱足,诸土色亦俱足,不务妍媚,而朴雅坚栗,妙不可思。以致于当时人认为:几案有一具,生人闲远之思。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,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,擅空群之目矣。虽然,时大彬之后没有出现空前绝后的大师,但陶肆谣曰:‘‘壶家妙手称三大‘‘,谓时大彬、李大仲芳、徐大友泉也。因为三人排行都是老大。李仲芳以文巧著称。徐友泉以毕智穷工,移人心目见长。他们两人都是时大彬的高足,被周高起列为名家。此外精妍的欧正春,坚致不俗的蒋时英,式尚工致的陈用卿,坚瘦工整的陈信卿,以及由仿制入手,渐入佳境的闵鲁生、陈光甫,均列为雅流。重锼叠刻,细极鬼工的陈仲美,善于造型、妍巧悉敌的沈君用,被列为神品。至于其他成就稍差的数人,则另为别派。周高起凭自己的识见,给明代的紫砂茶具制陶高手排出了座次。《阳羡茗壶系》不仅成为研究紫砂茶具史的珍贵资料,也成为茗壶收藏家、品茗爱好者的极为重要的参考书。J 明人对紫砂壶评价极高,视能够得到一把名壶为终身大幸。往时龚春茶壶,近日时彬所制,大为时人宝惜。(许次纾《茶疏》)有个名叫周文甫的,藏有供春壶,摩挲宝爱,不啻掌珠,用之既久,外类紫玉,内如碧玉,真奇物也。周文甫死后,有遗嘱将壶随葬(见闻龙《茶笺》)。生生死死,不愿分离,其爱壶之深,可见一斑。 《茶疏》还提出宜缀,即应停止品茶的情况:作字,观剧,发书柬,大雨雪,长筵大席,翻阅卷帙,人事忙迫,及与上宜饮时相反事。品饮不宜用的是:恶水,敝器,铜匙,铜铫,木桶,紫薪,麸炭,粗童,恶婢,不洁巾帨,各色果实香药。品饮不宜近的是:阴室,厨房,市喧,小儿啼,野性人,童奴相哄,酷热斋舍。对于来客,也很有讲究:宾朋杂沓,止堪交错觥筹。乍会泛交,仅须常品酬酢。情素心同调,彼此畅适,清言雄辩,脱略形骸,始可呼童篝火,酌水点汤。 许次纾所论,不仅指自然环境,还包括社会环境。作为品茗首要条件的,是心手闲适,而品茶又能解除疲劳,当披咏疲倦时,品茶的意趣和实用,就能统一在其中了。许次纾所强调的,包括品茶的心态、最佳时机、最好地点、助兴伴侣、天气选择等众多方面,使普通的饮茶提升到品饮艺术和审美情趣,使人们获得最大的愉悦。当然,品茗因对象不同,条件不同,要求也不同,《茶疏》就介绍了士人登山临水和出游远地的权宜之计。 40多年之后,冯可宾又在《〓茶笺》中谈到茶宜的13个条件。一是无事,神怡务闲,悠然自得,有品茶的工夫;二是佳客,有志同道合、审美趣味高尚的茶客;三是幽坐,心地安适,自得其乐,有幽雅的环境;四是吟咏,以诗助茶兴,以茶发诗思;五是挥翰、濡毫染翰,泼墨挥酒,以茶相辅,更尽清兴;六是倘佯,小园香径,闲庭信步,时啜佳茗,幽趣无穷;七是睡起,酣睡初起,大梦归来,品饮香茗,又入佳境;八是宿醒,宿醉难消,茶可涤除;九是清供,鲜清瓜果,佐茶爽口;十是精舍,茶室雅致,气氛沉静;十一会心,心有灵犀,启迪性灵;十二赏鉴,精于茶道,仔细品赏,色香味形,沁入肺腑;十三文僮,僮仆文静伶俐,以供茶役。《〓茶笺》还提出禁忌,即不利于饮茶的七个方面:一是不如法,煎水瀹茶不得法;二是恶具,茶具粗恶不堪;三是主客不韵,主人、客人举止粗俗,无风流雅韵之态;四是冠裳苛礼,官场往来,繁文缛礼,勉强应酬,使人拘束;五是荤肴杂陈,腥膻大荤,与茶杂陈,莫辨茶味,有失茶清;六是忙冗,忙于俗务,无暇品赏;七是壁间案头多恶趣,环境俗不可耐,难有品茶兴致。 许次纾和冯可宾提出的宜茶条件和禁忌,具体内容虽然有所不同,但核心都在于品。饮茶意在解渴,品茶重在情趣。当然,品茶还有其他讲究,如以客少为贵,客众则喧,喧则雅趣乏矣。独啜曰神,二客曰胜,三四曰趣,五六日泛,七八曰施(张源《茶录》)。饮啜之时,一壶之茶,只堪再巡。初巡鲜美,再则甘醇,三巡意欲尽矣(许次纾《茶疏》)。明代茶书反映的由饮茶到品茶的推移,从茶文化的整体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趋势。但是,当把这种追求导向极致,也就由明初的以茶雅志,单纯地走向了物趣,走上了玩风赏月的狭路,故晚明的茶文化呈现出玩物丧志和格调纤弱的倾向。oZ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明代茶书的内容,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茶书数量居多,内容庞杂,并且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误解,得不到应有的评价。详细地叙说,也许可以为读者进行一番导读,还可以拨去其蒙上的一些迷雾。总之,明代的茶书反映了茶艺的简约化和茶文化精神与自然的契合;明人撰写的茶书闪现着隽思妙寓的智慧,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。
标签:
文章均为安溪铁观音茶叶网发布,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:http://988133.com/view.asp?id=21124
安溪铁观音茶叶网
铁观音价格,铁观音茶叶价格表_安溪铁观音茶叶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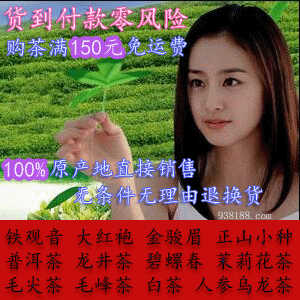
- 评论:(0)
- 隐藏评论
【评论很精彩,有内幕、有真相!】